葉浚生:大學裏的隱形戰爭——AI時代的教育範式轉移
香城大學圖書館的燈火在深夜依然明亮, 學生允行緊盯著螢幕,指尖不自覺地敲擊著鍵盤邊緣。DeepSeek對話框裡剛生成的論文段落流暢得近乎完美,卻也完美得令他心虛。他咬咬牙,將文本複製到另一個AI工具,看著它被拆解、重組、刻意加入不自然的停頓和彆扭的用詞,彷彿在對一段「過於聰明」的文字實施某種「降智手術」。螢幕右下角,網頁工具的檢測視窗靜靜閃爍,像一臺無情的測謊機。「AI生成率:14%」——紅色的數字刺進他的視線。允行低聲咒罵,手指飛快地在鍵盤上敲打, 他必須在提交期限前,把這個數字壓到教授規定的5%以下。不遠處,二年級的家寶嗤笑一聲,螢幕上同時開著Gemini、ChatGPT、Grok和一個語法錯誤生成器。「你這樣太慢了」她頭也不抬地說,手指滑過觸控板,像指揮官調度軍隊,「讓AI改寫AI,再手動加幾個錯字,教授根本分不出來。」圖書館的玻璃窗映出他們彎腰駝背的身影,彷彿兩名黑客在深夜入侵某個學術系統,而系統的另一端,教授們正高舉Turnitin的檢測報告,宣稱自己贏得了這場「反AI作弊戰爭」。他們都沒意識到,真正的戰爭才剛開始。
雖然上述故事的情節略顯戲劇化,但這種『AI對抗AI』的荒誕現象,本質上暴露的是教育體制在科技變革中的結構性失能。這種「AI對抗AI」的現象,反映的或許是教育政策與科技發展的脫節危機。翻查立法會最新文件,教育局近年雖已更新《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2024年),並在小學高年級及初中推行人工智能和編程的增潤課程,但對制定本地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引》仍態度模糊。官方僅表示會「持續參考各地發展」來更新課程,卻未具體說明如何將國際經驗與香港獨特的雙語教學環境、應試文化相結合,令人憂慮政策能否真正切合本地教育實際需求。
幾位在中小學任教的朋友告訴我,雖然人工智能課程單元涵蓋人工智能基礎、人工智能倫理、社會影響和未來工作等不同內容,但當真正面對應用生成式AI時,學校往往選擇禁止。學生就像「從未踢過足球的人大談戰術」,缺乏實際操作經驗的「倫理體驗」便顯得蒼白無力。一位資深教師直言:「再多的創新教學,最後都要回歸到背誦標準答案的現實。」問題的根源, 在於香港教育的終極目標仍是公開考試。當AI已能完美複製考試範文,我們的中學教學卻仍在訓練學生進行機械記憶。這種荒謬的落差,導致那些好不容易通過考試進入大學的學生,立即陷入「用AI作弊」與學業壓力的兩難困境。說到底,不是學生不想誠實,而是整個教育制度引導他們在灰色地帶遊走。
歷史或可為AI時代提供啟示。1970年代,當第一臺電子計算機出現在美國時,教育界爆發激烈爭論:「如果學生連基本運算都依賴機器,他們還剩下什麼能力?」 當局一度全面禁止計算機,要求學生死記「四位數表」,在考場上手算平方根與對數,彷彿「算術能力」等同於「數學思維」。諷刺的是,十年後,計算機不僅獲准進入多個公開試的考場,更成為數學課程的必修工具。教育者終於明白:當機器能處理機械計算,人類的價值不在於「按對按鍵」,而在於「問對問題」。今日的AI浪潮何嘗不是如此?
這種似曾相識的場景正在當下重現。就在教育者仍在為AI定位爭論不休時,已有學生開始挑戰學術倫理的邊界。最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畢業典禮上,有一位畢業生公開向著電視台攝影機前展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對話界面,「得戚」明示ChatGPT幫他完成畢業論文,此古怪行徑近乎挑戰大學抨核學生的底線。這一幕正好突顯在AI時代西方教育對學生使用AI規範的定位模糊。
AI時代的教育正面臨根本性的範式轉移,這種規範模糊的困境實則揭示了更深層的核心矛盾。當生成式AI已徹底重塑知識獲取的途徑,若教育體系仍固守於「防堵」與「檢測」的傳統思維,只會陷入一場永無止境的技術軍備競賽。破解此困局的關鍵,在於從根本上重新定義教育的本質:與其糾結於如何防止學生使用AI,不如積極思考如何將AI轉化為學習的增效器。
這要求教師角色必須實現從「知識權威者」到「學習架構師」的根本轉型,成為引導學生與AI協作的「導航員」,在數位浪潮中把握學習方向;化身為學習旅程的「同行者」,與學生共同探索AI時代的知識建構新模式;擔當思維能力的「鍛造者」,重點培養演算法無法替代的元認知與批判性思考;更要成為創新潛能的「催化劑」,引導學生在AI生成的基礎上實現創造性突破。
香港教育在這一轉型中具有獨特優勢。其制度彈性能快速響應變革需求,悠久的師道傳統為角色轉型提供文化根基,完善的數位基建則為技術整合創造條件。這種以「人機協作」為核心的教育範式轉型,不僅是技術應用的調整,更是教育哲學的重塑。當西方教育仍在AI使用的道德爭議中徘徊時,香港若能建立兼具倫理嚴謹性與創新活力的「智能教育框架」,明確界定AI在教育中的應用邊界與深化路徑,或將開創出一條超越傳統東西方教育二元對立的新道路,為全球教育轉型提供具有東方智慧的解決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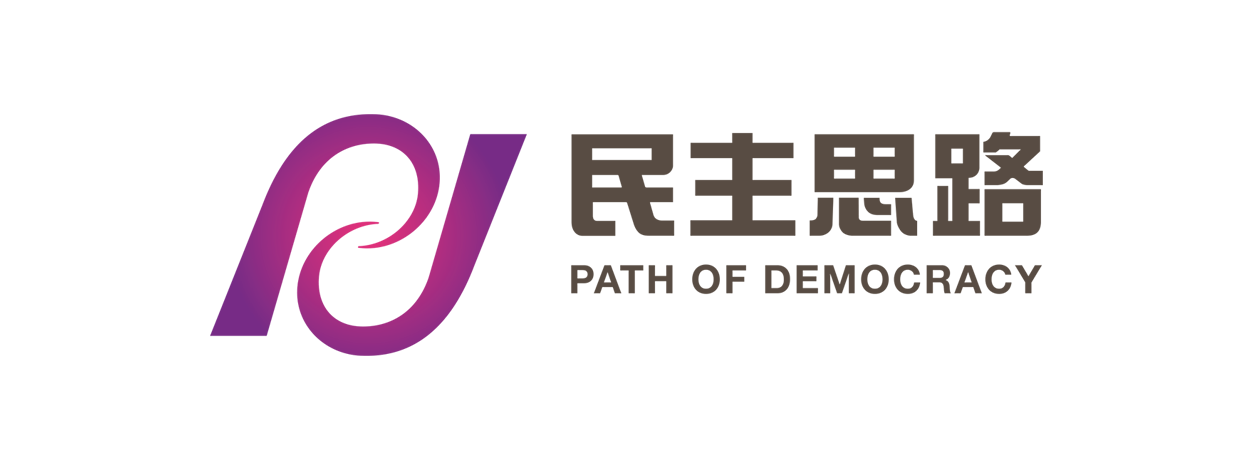
 EN
EN Login
Login Donation
Donation

 Back
B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