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日報 |A12 | 每日雜誌 | 慎思而行 | 龍家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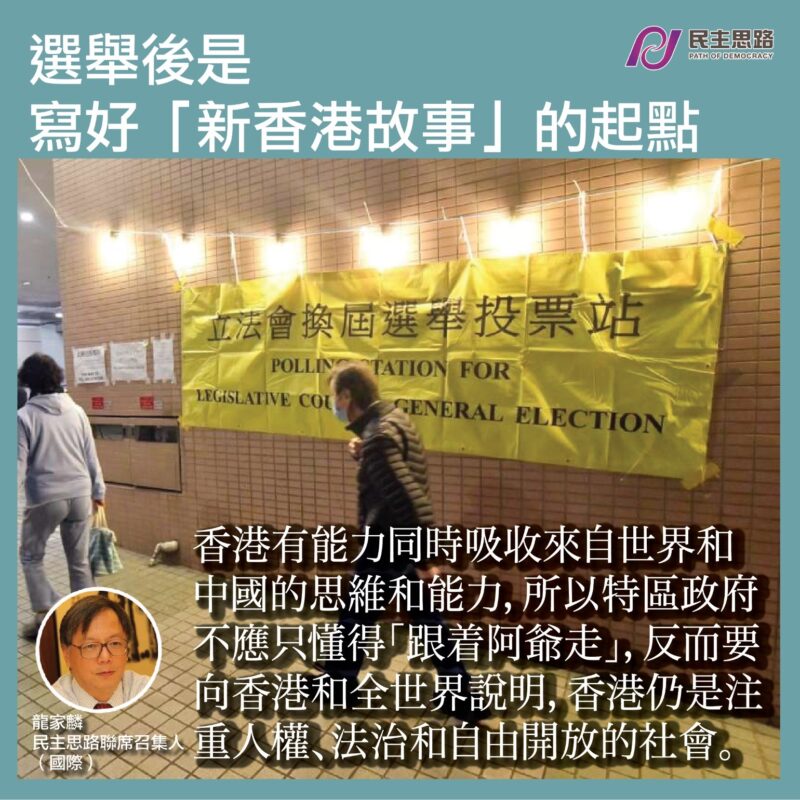
《基本法》原來構思是由一個沒有政黨背景的行政長官和高質素的公務員團隊去管治香港。過去二十多年經歷的社會動盪,包括「反國教」和「佔領中環」,說明了這構思有不少漏洞。反對「逃犯條例」的暴力示威,引發中央出手,實施港版國安法和制定立法會新選舉方法。事情表面上似乎過去,但一直存在的內部問題仍未解決,加上連骨子裏都是「自由主義」的香港,也逃不過美國的制裁,失去了一九九二年定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優惠待遇,個別官員包括特首林鄭月娥亦被美國制裁。
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二○一九年在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發表文章,預言香港希望同時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的 「國際城市」和「中國城市」將會遇上不少困難。拜登和布林肯主持的首屆「民主高峰會」似乎說明了鷹派勢力正在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熟悉中國和主張透過外交接觸去解決問題的官員,未必能夠扭轉現時美國國會和白宮官員的世界觀。從廣泛的角度觀察,主張敵我對壘的「主戰派」,從來存在於美國政壇和「深層國度」(Deep State,指政府官僚和軍事工業所組成的複合體)。香港處於中美博弈間一個不利位置,失去「中國國際金融中心」的潛在的危機,也隨着八家中國企業,遭美國以侵犯人權為理由,啟動「金融脫鈎工具箱」而浮現到表面。
爭取扮演「中國未來發展實驗室」
各國(包括中國)的外交政策,往往也優先考慮國內的政治需要。當各界對美國涉港政策作出強硬回應時,似乎還沒充分確認到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經濟體,向來沒有還擊能力。正是由於這特性,香港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之中扮演了「引進來」的角色。一位精通俄語和中文的美國外交官曾經在香港民主促進會演講中指出,如果戈爾巴喬夫當年有一個小小的香港,前蘇聯的 「改革開放」Glasnost and Perestroika必定會取得更大成就。香港和中央駐港官員也需要了解過去,確認過去不少「改革開放」的思維是源自香港,並且共同領導香港面對國際形勢的演變,走出「兩難局面」。
立法會選舉剛剛結束,接着下來的就是特首選舉。選舉過後就是張炳良教授說的「二次過渡」的開始,香港需要在「一國兩制」之下,尋找一個各方都能夠認同的「新香港故事」。李光耀當年決定不拉倒新加坡第一任總督萊佛士 (Sir Stamford Raffles) 的銅像,是向全世界表明新加坡了解過去,並且會積極面對未來。下屆政府管治好香港的經濟,民生和社會發展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在大國博弈中間,香港的前途不能與中國對立,無論國際社會對香港的看法是怎樣,我們只能夠站在中國的一邊。但是,香港有能力同時吸收來自世界和中國內地的思維和能力,所以特區政府不應只懂得「跟着阿爺走」,反而要向香港和全世界說明,香港仍然是注重人權、法治和自由開放的社會。民間智庫和政府也應該對最新發表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作出積極回應,向中央爭取實現《基本法》承諾的「普選」和盡量用好香港的國際視野在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之中,尋找一個不可或缺的角色,爭取繼續扮演「中國未來發展實驗室」,並且開始以「中國香港」身分向全世界講好「新香港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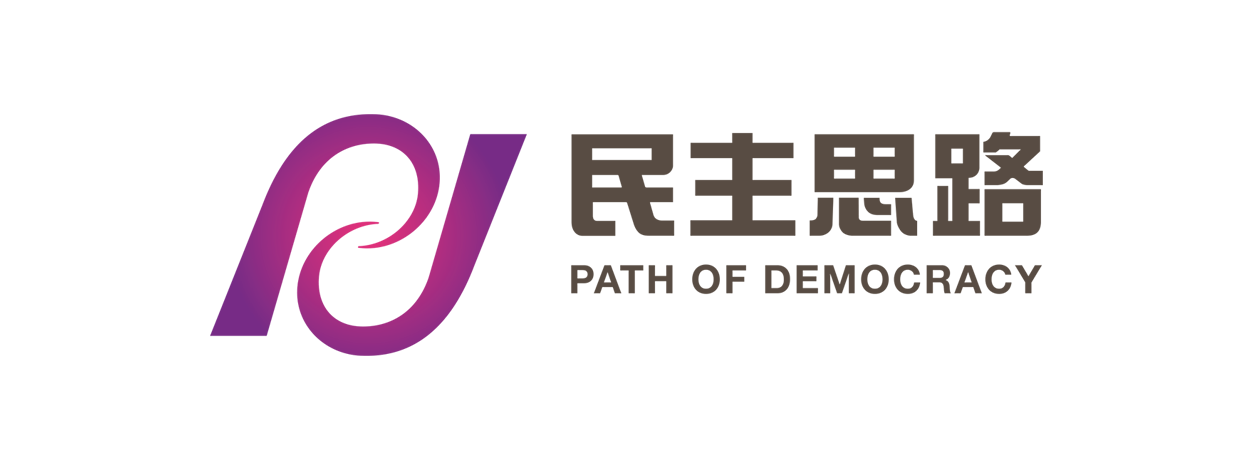
 EN
EN Login
Login Donation
Donation

 Back
Back